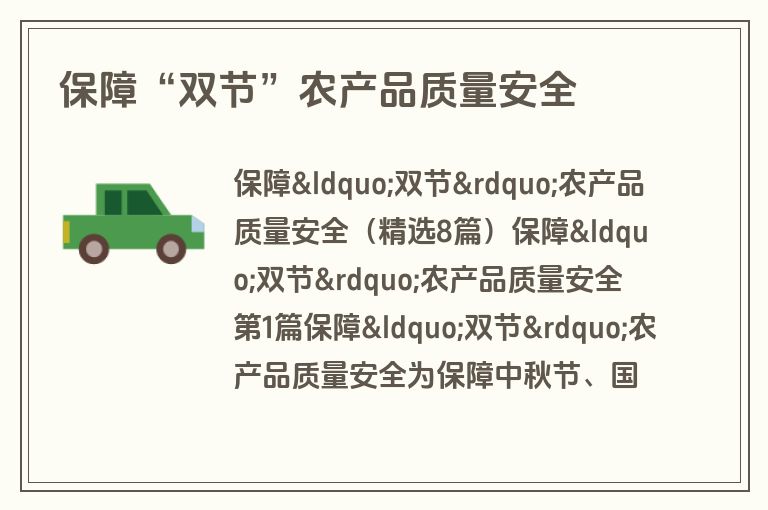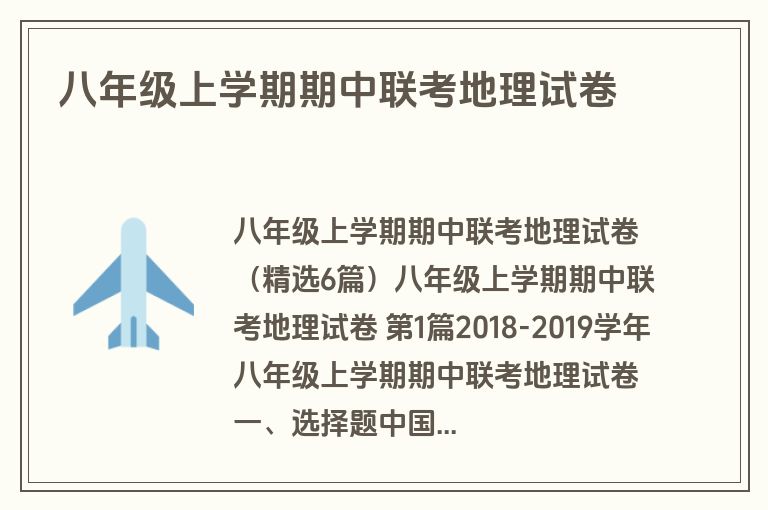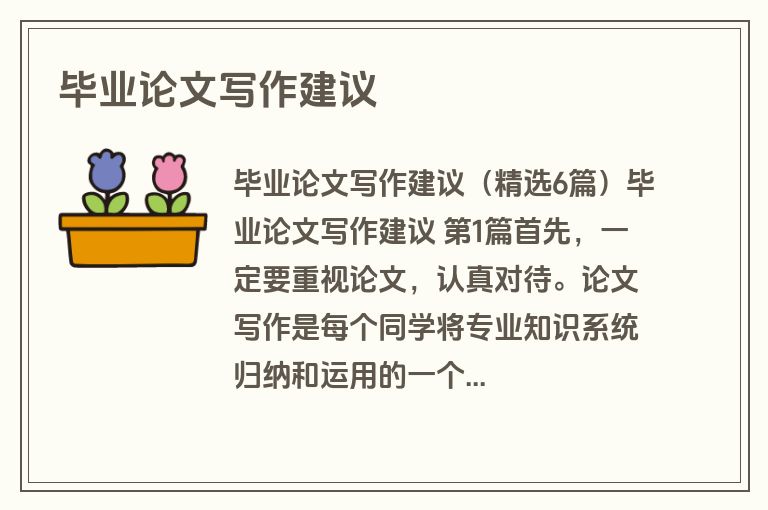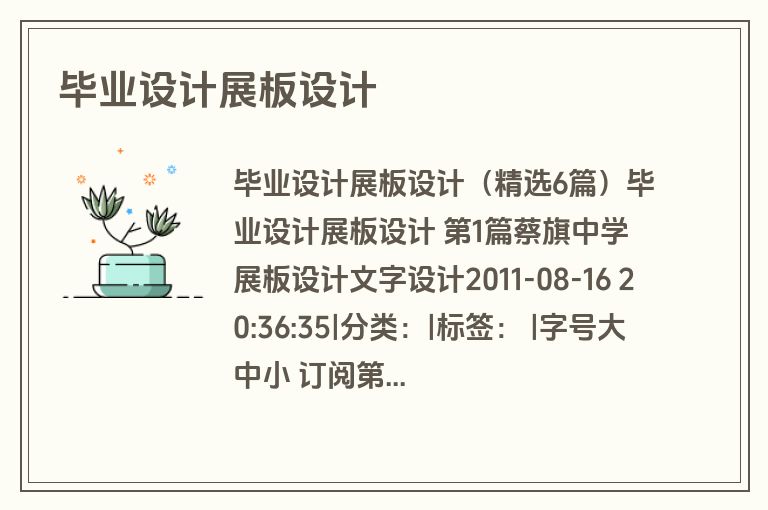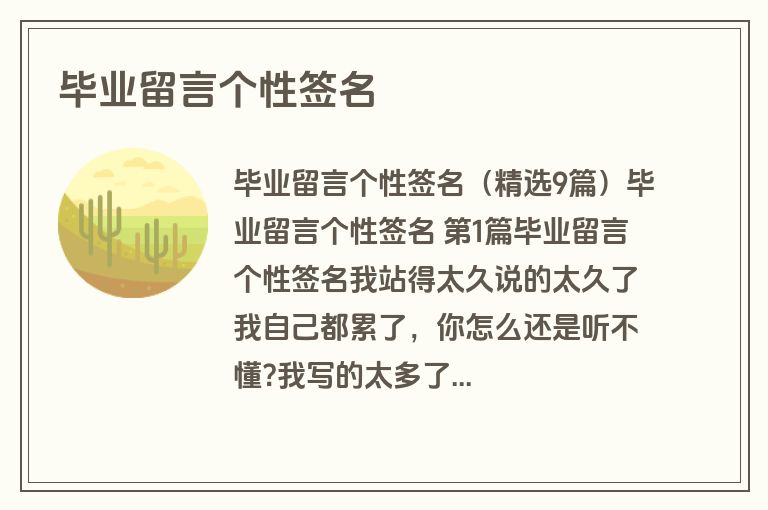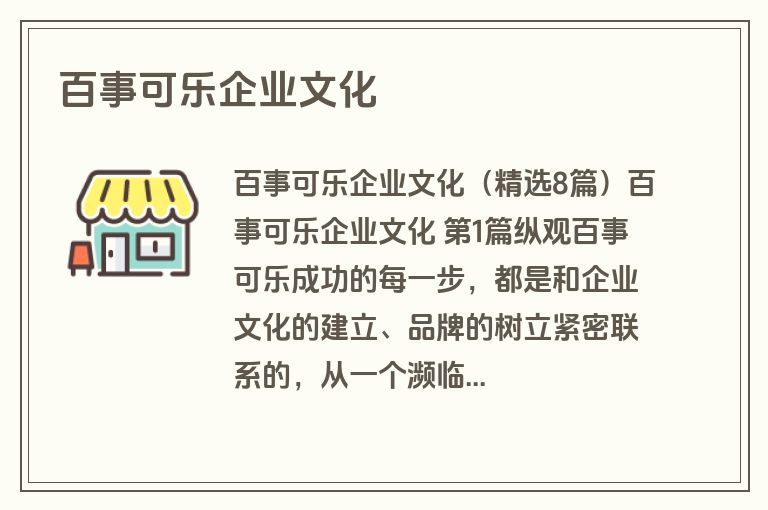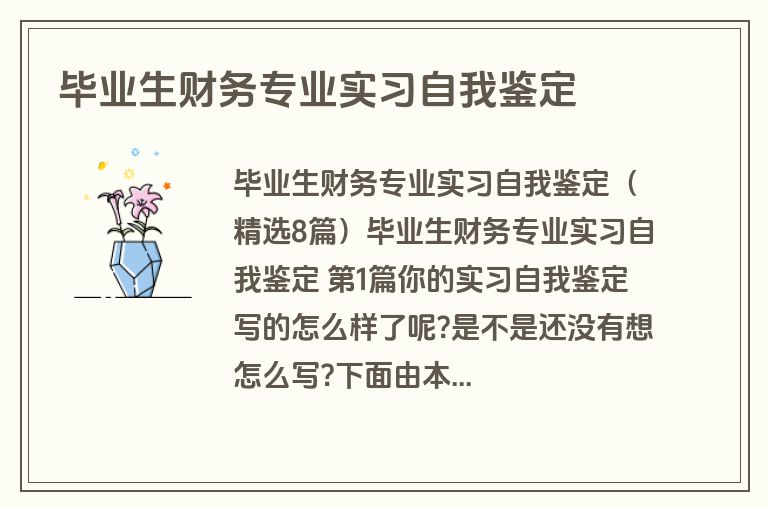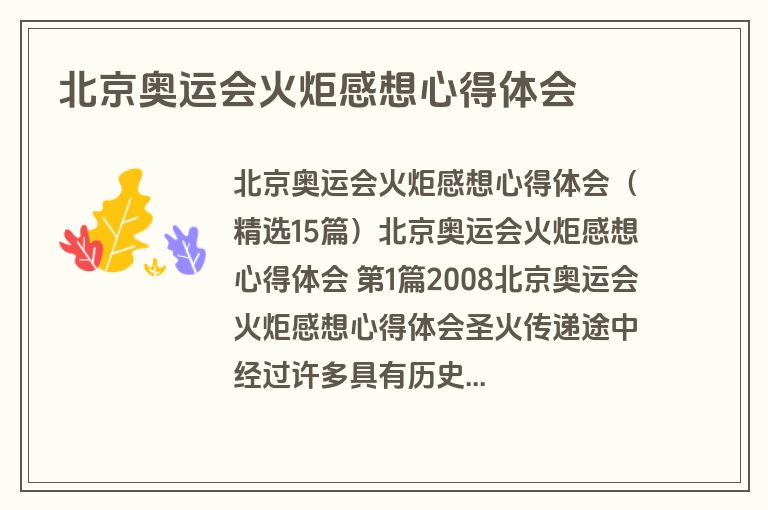爱唱秦腔的父亲亲情散文(精选3篇)
爱唱秦腔的父亲亲情散文 第1篇
前些天整理书柜时偶然翻到了一个戏本子,拿在手里仔细端详,认出那竟是父亲20多年前唱秦腔时用过的剧本。
父亲一生酷爱秦腔,但时运不济,在他很小时爷爷就去世了。因家里穷,没上过学,识字不多。好在解放后政府办农民识字班,父亲参加后学了些,到了勉强能看懂报纸的程度。虽然文化程度低,但并没影响他唱秦腔的嗜好。据了解他的老人们给我讲,父亲在旧社会时曾拜师学过戏。这几年,以前跟他一起唱过戏的人也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起过他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唱戏的情景,言语间颇有赞誉之辞。
我记得父亲唱戏是在改革开放初的那些年,随着党的富民政策的深入人心,家乡的戏剧事业着实红火了起来,父亲自然也就成了推动家乡民间文化发展的热心人。
那几年,一到冬闲时节,父亲便和村里的几位老秦腔爱好者组织大家排戏,地点在一个废弃的村办企业的车间里,我曾跟去看过几回。天寒地冻的腊月天里,偌大的车间里只有一个火炉,可每个人都练得头冒热气,大家的精神头可足了。
拍戏时最大的困难是没有剧本,父亲便和大家商量决定自己刻印,这对于一帮如父亲一样的农民来讲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他们没有丝毫的胆怯,买来铁笔、蜡纸、油印机等刻印工具分头工作,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还真的刻印了出来!而且在以后的几年里,又陆陆续续地刻印出了好几本,如《三世仇》、《下河东》、《升官图》、《三滴血》等,父亲在这些戏里都出演过角色。
父亲把他们刻印出的剧本真的当成了宝贝,在中午和晚上吃饭的时间里,入户的有线喇叭里有时也播放秦腔录音。每到那时,他就会赶紧拿出剧本坐在门槛上跟着唱,我们谁也不敢打搅他,而他唱得常常是忘记了吃饭,顾不上休息,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
时间很快就进入了正月,大年初三过罢,就是唱戏的时节了,不但自己的班子唱,也邀请周边村子里的班子来唱。这时的父亲就完全成了一个大忙人。因人缘好,自己唱时他是组织者,邀请别人唱时他又是联络者,家里家外、白天黑夜、台前台后总是忙得不亦乐乎,一直忙到过完年。他和自己的草根戏班子曾经为乡亲们的春节活动带去了无限的欢乐。
憨厚朴实的父亲,一生最精彩的表现也许就是他唱戏的经历了。戏台上的父亲,或许没有华丽的造型,没有优美的唱腔,有的只是他对生活和秦腔艺术执着的爱。人生如戏,父亲将他对人生的理解、将他的喜怒哀乐都寄托在秦腔里面了!
父亲离开我们已有九年多,他的人生虽已谢幕,但他乐观开朗的性格特征和热情诚恳的生活态度已经成为了我们受之不尽的宝贵财富,我将把父亲留给我的剧本和他爱唱秦腔的精神一起珍藏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怀念我爱唱秦腔的父亲!
爱唱秦腔的父亲亲情散文 第2篇
关键词:寻根文学,民族文化,文学创作
在我国现当代文学史上, 曾出现过一种被称为“寻根文学”的文学思潮, 它在中国文坛上曾掀起过一股“文化寻根热”。这个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文学热潮, 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许多作家和读者对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思考和热议, 而且直到今天这种文化上的寻根求源也没有停下脚步。
“文学有根, 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 (1) 。在众多的关乎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文学作品之中, 似乎西北作家这个“团体”永远不能被我们忽视。而在众多的西北作家当中, 有一个名字显得分外醒目, 他的作品一向以纯粹、平实的语言, 浓重的秦地情节给人以强烈的印象, 他就是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贾平凹。
秦人贾平凹, 对于秦地的热爱、对于秦文化的思考, 我们从其散文、小说中都能够了解到。这其中, 我想, 他的散文作品《秦腔》可以被视作分析贾平凹“寻根”情愫的很好例证。当然, 这似乎和已然被我们认作是寻根文学代表作品的贾平凹的《商周系列》有着一脉相承的地方。
我喜欢从“秦人”、“秦地”和“秦腔”的三者关系来读这部作品。这主要也是因为我在阅读贾平凹其他作品的时候发现, 他的情感及其所生发出的文字都源于对秦地文化的深厚热爱。由此, 我们不禁想到文学史上,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寻根作家”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都触及了作家们对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和对传统文化意识的思考。
“山川不同, 便风俗区别, 风俗区别, 便戏剧存异”。《秦腔》中, 作者在开篇就给了我们他自己对于地域文化的理解。显然, 作家的思考是很受大家认同的。
这篇文章的结构思路很清晰, 由议论展开、夹叙夹议;先后写了等戏、看戏、议戏的场面, 生动、形象, 有感染力。想必给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这种场面的描写, 地域色彩浓厚, 给读者一种对秦地、秦人、秦腔的感性认识。而透过这些作品内容, 我们能够看到的更有秦川一带文化具象后的影子。秦地自然条件的恶劣连结着秦人悲苦而又奋争的生命;秦人的释放和粗犷又造就了秦腔“吼”的艺术。秦人、秦地、秦腔就在这种必然的联系中完成着一次又一次的生命延展, 绵延千年而历久弥新、生生不息。
也许, 有人说“文化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我不否认这种观点, 我只是想明确一个小问题, 即文化的交流和借鉴一定不可忽视自身文化的价值。
“寻根文学”, 乃至“文化寻根”不是复归传统, 而是为西方现代文化寻找一个较为有利的载体。
在对于西方现代文学历史和作家的状况有了较多了解之后, 迫切要求文学“走向世界”的作家也已经意识到, 追随西方某些作家、流派, 即使模仿的再好, 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艺术创造。在他们看来, 以“世界文学”的视镜从中国文化寻找有生命力的东西, 才应该是中国文学更为可行之路。而这种“寻找”, 正是“寻根文学”曾经做出的有力探索, 正是像《秦腔》这样的文章背后隐含的、给予这个时代的巨大诉求。
在当今这个城市现代化、乡村城镇化的时代, 我们见到的是街道两旁西式建筑林立、高校教舍竞仿白宫。那些涵养国人千年的民族文化也似乎止于考卷而距我们渐行渐远。这种退变是对自身文化忽视的必然。文化就似植物, 倘若只顾枝叶而不重根基, 那么再艳丽的枝叶也只是表面的繁荣。
“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 或已转易, 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民族生命, 至于今日岿然独存” (2) 。我们应当珍惜这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 珍视民族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 凡是都要立足正反两面去看待。从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以来, 寻根文学的兴盛在文学上引起了很多寻根作家在创作时吸收了大量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方式, 在促进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上功不可没。在文化上, 也引起了人们对文化继承问题的思考。但是, 大多数作家对"文化"概念的理解是"以偏概全"的, “他们往往抓住某种民俗、习惯便刻意进行渲染, 而忽略了对"民族性"的真正解剖。尤其是一些作家对现代文明的排斥近乎偏执, 一味迷恋于挖掘那种凝滞的非常态的传统人生, 缺乏对当代生活的指导意义, 而导致作品与当代现实的疏离, 这造成了几年后"寻根文学"的衰微”。这也启示我们如何在外来文化影响和自身文化有效传承之间摆正自己的位置;如何平衡这种关系。
我想, “寻根文学”所带来的“文化寻根”可以被视作为一种文学干预现实的努力。“寻根文学”和“寻根作家”的认识饱含着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 同时也告诉我们在分析现实问题时, 不应当、也不能忽视文学作品的智慧。
参考文献
[1]韩少功《文学的“根”》1985年刊于《作家》[1]韩少功《文学的“根”》1985年刊于《作家》
爱唱京剧的父亲 第3篇
后来家里买了电视,常有京剧节目播出,父亲可乐坏了,守着电视可以连饭都不吃。那时我们很不理解父亲,不明白父亲为什么对那已经过时的文化那么感兴趣。而我们全家都喜欢看现代节目,所以我们常和父亲抢电视,父亲拗不过我们的时候就会到别人家去看,还好也有同父亲一样爱好京剧的邻居。
父亲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戏友,有空的时候,他们便会聚在一起相互交流,学习京剧的唱腔,哪怕唱得不好也要唱上几段自娱自乐。而母亲对父亲唱京剧的声音特别反感,每次父亲在家里想唱上几句时,母亲总是大声呵斥,骂父亲是老古董。而我和母亲一样,从小到大对京剧都没兴趣。
如今我已成家立业,而父亲也老了,我所在的城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剧院里再也没人来唱戏,只有明星的演唱会,就连电视也很少有这类节目。父亲却一直保持着这种爱好,而且进步不小,还和一些京剧爱好者一起,组建了一支属于自己的专业队伍,各种乐器都齐全,每到周末便会到公园齐聚一堂,痛痛快快地唱上几段,不仅唱京剧,还唱黄梅调等多种戏剧。观看的人也不少,可走近一看,你会发现这里看不见年轻人的身影,只有老年人在观看,每到此时,我总有一丝担忧,哪一天父亲和他的戏友唱不动了,在公园里还会听到这种声音吗?这可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传统文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