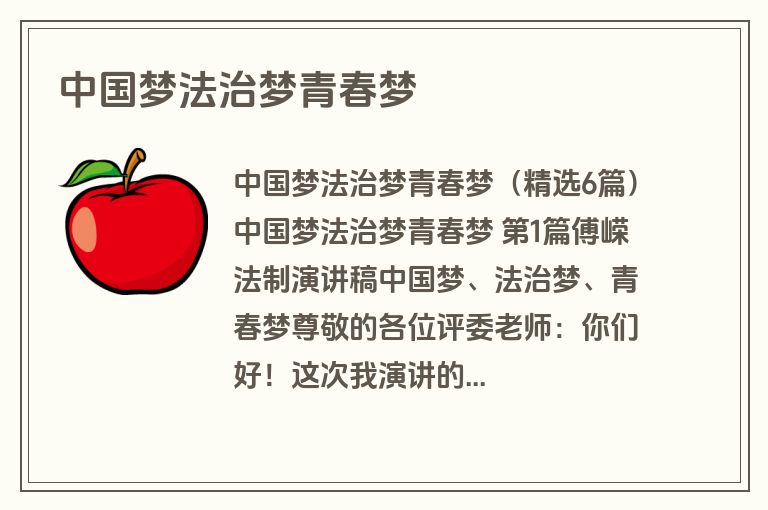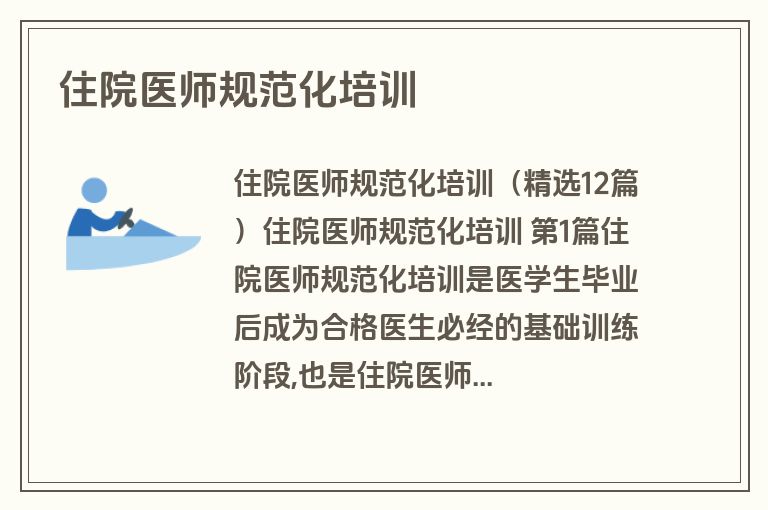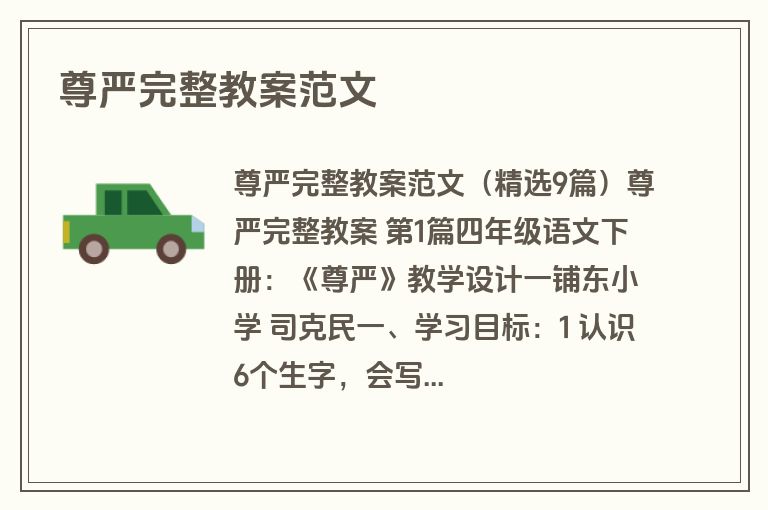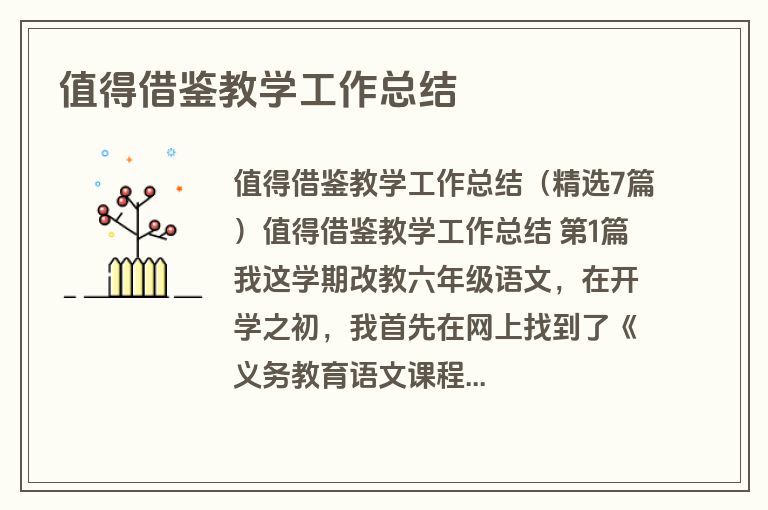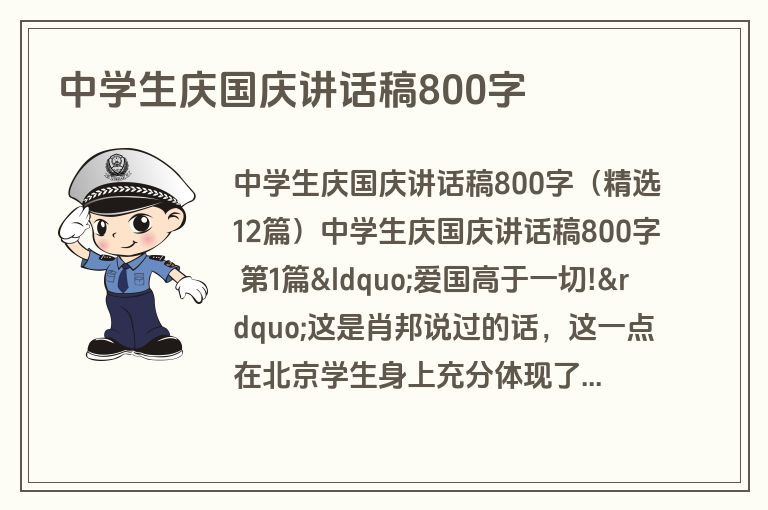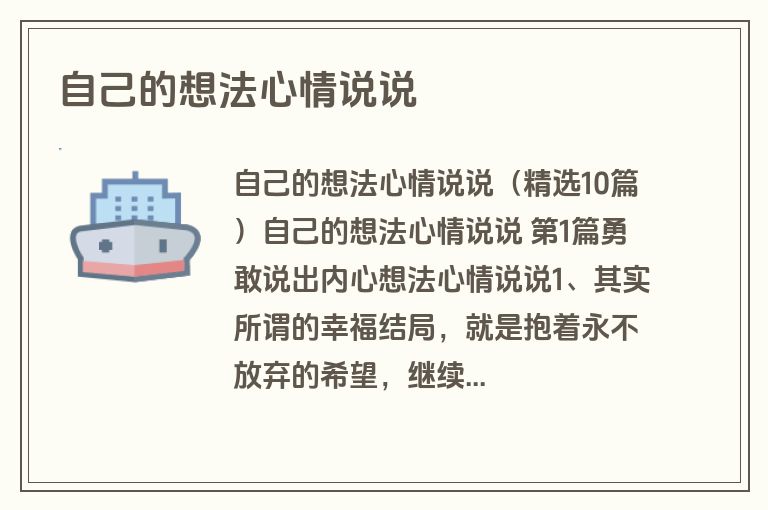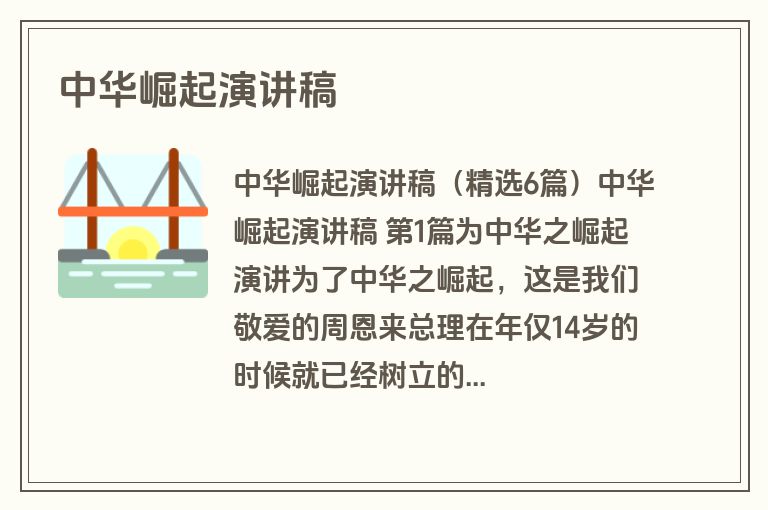王朔小说论文范文(精选3篇)
王朔小说论文 第1篇
(一)文学产品多元化下的冲击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定型,文学的商品化和世俗化愈加突出,既然是商品化,那么必然会依据商品模式进行批量生产,这就造成了作品数量、类型的大幅增加。如果说当初八十年代大陆的通俗文学还靠港台文学的传入才能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的话,那么现在文学产品的多元化足以满足读者各式各样的需求。就小说而言,言情、武侠、宫斗、穿越、悬疑、都市、乡村、官场、科幻等等各类题材几乎是应有尽有,而且针对不同的性别、年龄、阅读层次都有海量的作品出现。
不仅文学类型多元化,文学的载体也是日益增加。报纸期刊杂志等纸质读物已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在科技的推动下,网络文学的盛行不仅给作家提供了便捷的平台,也可以让读者直接在网上就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品,而且读者能够即时评论并和作家达成对话,作家作品读者的距离大大拉近。另外,近几年手机读物的出现更是让人们在随时随地都能够接触到文学,文学不再是束之高阁,而是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在多元化的文学产品丰富文学市场的同时,也造成了文学自身的平面化、碎片化。一个作家、一部作品要想脱颖而出产生轰动效应几乎是难于上青天,这不仅是文学自身的多元化造成,也与传播媒介的多元化有关。上个世纪,报纸、杂志、书籍影响着人们的业余生活,而当今电视剧、电影、话剧等等充斥着人们的闲暇时光,在这个读图的时代文学逐渐趋于边缘化。所以说在这个文学边缘化而又多元化的时代中,作家、作品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王朔自然也不例外。一个作家要想获得长久的发展就必须以作品说话,不仅作品内容要符合读者的阅读需求,形式也要不断变化,如果都是千篇一律,那么有什么理由让读者在多元的选择下去欣赏这种重复呢。而王朔此时的表现又是如何呢?
(二)王朔小说创作的自我束缚
在面对众多的文学作品时,我们再看王朔以前的小说,语言的滑稽调侃让人们不再感兴趣,反而觉得有种刻意和迎合,而且情节简单,模式化突出。比如他的小说基本都是沿着“爱情”和“案情”的道路发展,在这个产品多元化的时代中让人觉得枯燥乏味。另外,在王朔复出时大肆借媒体宣传自己,以至于他的以佛经为材料的小说《我的千岁寒》被伦敦书屋以每个字三美金的价钱购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个高昂的价钱下的作品并没有引起读者的轩然大波甚至被读者所批判。
从《看上去很美》开始,王朔似乎有意识地想要转换一种风格,不再刻意地去迎合市场和读者,而是转入内心去追寻“深度”。在《我的千岁寒》《新狂人日记》《致女儿书》《和我们的女儿谈谈话》中,故事情节逐渐淡化,更多的是王朔自身对人、对事、对生、对死的看法,带有浓厚的“自我”色彩。由于对哲理化的深度追求,这些作品不免带有一种“概念化的阐释和演绎”,为了阐述这个概念,以这个概念为前提去组织故事,这样的故事说教意味浓厚,而且结构松散,语言也不再是从前的调侃幽默而趋于自我化。然而在当今这个浮躁的年代,并没有多少读者愿意去沉下心来细细欣赏这其中的深刻性。
纵观王朔的小说创作历程,最初的纯情小说为了赚取读者的眼泪,如《空中小姐》复员军人和空姐的悲剧的爱情故事为人所触动;之后的一系列作品在市场的导向下把文学当成商品来创作以供读者消费,把小说的消遣娱乐性发挥到极致;最后笔锋转向心灵,具有自我审判的意味。对于王朔而言,他的每个阶段的不同追求使他的创作显现出不同的风格,而对于读者而言,在乎的却不是他的追求,而是根据自身的阅读需要来选择自己的阅读产品。
虽然市场的发展和小说自身风格的束缚导致了王朔小说的逐渐式微,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王朔热”现象,这些足以使他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摘要: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王朔无疑是文坛上大家关注的焦点。他的小说创作,影视参与以及充满个性的文学评论所形成的“王朔现象”已远远超出了文坛的范围。然而,在当下王朔似乎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他的小说也不似当年如此受读者追捧,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比如文学产品的多元化对他的小说的冲击;王朔小说创作自我风格的转变等等。
关键词:王朔小说,式微,产品多元化
参考文献
[1]吕周聚.现代市场经济语境中的文学悖论——王朔现象透视[J].烟台大学学报,2002,(2).
[2]刘安海.通俗文学的趋众性与模式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6,(4).
透过《顽主》谈王朔小说的先锋性 第2篇
摘要: 本文主要以王朔小说代表作《顽主》为例,通过对人物、语言、风格三个方面的阐释,论述了王朔小说的先锋性。
关键词:先锋性、颠覆性、调侃、顽主
王朔其人惯以被同行称作“文坛异类”、“痞子作家”的代表。其小说自1984年《空中小姐》在《当代》成功发表便一发不可收拾:《浮出海面》、《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动物凶猛》等小说也相继问世,并结集出版。《王朔文集》、《王朔自选集》在当时非常畅销,一时“洛阳纸贵”。他的许多作品像《动物凶猛》、《顽主》、《过把瘾就死》等还被改编为影视剧,在当时引起很大轰动。
许多评论者对于王朔的作品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俗”,何以谓俗?无外乎其作品颇多言情之类、颇多污秽之词、颇多玩世之举。但这只不过是就其表面现象品论而已。我觉得王朔的小说是“俗而不俗”即通俗但不庸俗;“雅而不雅”即极富生活化而且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也即他的小说是具有先锋性的。
《顽主》发表于《收获》1987年第6期,后改编为同名电影,是王朔“顽主”系列的代表性作品。作品虚构了一个“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极尽嘲讽、调侃之能事,对生活尽情的嘲弄和否定。以于观为首的几个青年人,替作家宝康策划并举办颁奖晚会,替不能按时赴约的人去赴约,替不能满足妻子对多方面要求的丈夫陪其夫人聊天、挨骂等。作品塑造了于观、杨重、马青三个主要人物以及与其有各种业务关系的宝康、刘美萍、王明水等各色人物,通过对人物的描写和故事的讲述,集中反映了这个社会中的一些特殊现象,揭示了社会的一些弊端,同时,对社会上的一些现象进行了嘲讽。
下面我以王朔的代表作《顽主》来具体探讨其小说的先锋性。小说主要讲了主人公即三个顽主开了一家专为人排忧解难出主意的“三T”公司,以及在经营这个公司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既喜剧又戏剧性的故事的事。我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论《顽主》是如何体现王朔小说的先锋性的。
首先《顽主》中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具有先锋性的。
《顽主》中着重塑造了三个顽主:于观、马青、杨重的形象,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了解什么叫玩世不恭,什么叫举手投足间的把不在乎,什么叫不学无术游戏人生。当然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细读小说我们就会体味出这些顽主身上的可爱之处和作者在小说中对他们无处不在的欣赏。他们思想纯洁,开心就笑,生气就骂,不矫饰,不造作;他们之间坦诚相待平等相待;他们的友谊是真挚的美好的。书中于观这样说:“他们是我最好的朋友,和他们在①一起我总是很快乐。”这是于观发自肺腑之言。他们心地善良,虽然爱开几句过分的玩笑话,但也仅限于玩笑而已。他们在遇到不顺心事时有着一颗谅解和宽容别人的心。书中曾有这样一段描写:顾客托于观退衣服,结果因为领子脏了不给退,于观就只好自己穿了。这说明他们的内心是善良的。他们聪明机智、敢想敢干,虽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他们有头脑、有想法。他们开的“三T”公司就很有创意,而且生意也是不错的。况且像“人生就是那么回事,就是踢足球,一大帮人跑来跑去,可能整场都踢不进去一个球,但还得拼命踢,因为
②观众在玩命地喝彩打气。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这样通俗但却寓意深刻的话不是随便一个不学无术的毛头小子就能说出来的。作家有意抬高这些顽主的形象,可以说是有其深意的。这些顽主无疑是作者一贯所关注的社会边缘人,他们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也得不到家长应有的关心。主人公于观整天泡在公司里而不愿去见那位一 脸严肃的老爸就是证明。按照传统的观点这些顽主是家长眼中的坏孩子也是游离于社会的渣滓。作者显然有他自己的爱憎,在“文革”结束,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下,作者看到了应该说感同身受到了那一时代青年的彷徨,作者理解他们同情他们。对于顽主所持的欣赏态度,也正是作者对来自于社会来自于家庭的一种真正的博爱和真正的人文关怀的呼吁。从这一点来说王朔的小说是具有先锋性的。在三个主人公的身上,对于信仰的概念似乎不太明显,他们打着“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受过”这一崇高的旗号,却做出种种放浪形骸、恣意妄为的事。他们用咸菜坛子给“作家们”颁发“三T”奖,让各色人物滥竽充数娱乐大众,在吃饭时把擦手毛巾塞脖子里,否定例行的餐前宣言、用轻蔑与不屑的眼神对待伦理家们虚伪的说教,自嘲“我们不过是一群俗人,饮食男女”,“我们什么也不干”,自我标榜“我们没什么烦恼,从来不看书,也就不烦恼了。”对于人类几千年建构的伦理道德、崇高理性全盘怀疑与否定,类似于后现代主义的解构思想。难道他们真的没有自己的内心的价值取向与精神信仰吗?难道他们也类似于“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吗?
事实上,他们肯定不是整天无所事事,三替公司就是个明证,他们不但看书,而且对于资产阶级、共产主义、国家大事、世界形势知道的一点不少,甚至于还对尼采、弗洛伊德等精神领域的深层阐述有所接触。关于自己的内心他们一点不糊涂,只是“当作为个体的人感到自己无力去获取某种价值时,很容易走向同否定和诋毁价值本身„这样一来,价值关怀就
③转为价值盲从与价值虚无。”这时候,他们有一种人生的孤独感、失落感。他们 “踏踏实实、本本分分、规规矩矩地生活,比起那些倒爷、违法乱纪者,比起那些利用权势投机的人,他们要诚实可爱得多。”于观对小鲁也像是对自己对所有其他看不起他的人说:“我看起来像在轻飘飘慢吞吞的下坠,可是你知道吗?我灵魂中有一种什么东西得到了升华。”在道德传统与浮华文明的双重挤压下,他们用表面上玩世不恭的做事方式去满足内心对于理想的守望,对于世俗的颠覆,对好好活着这一信念的阐释。他们并没有垮掉,而更像是塞林格笔下的麦田守望者,守望着自己心里的一亩田一亩地,用它来种下自己的人生理想,生命价值。于观他们虽然创办了一个荒诞不经、滑稽可笑的“三T”公司,但这同样源于他们内心对于自我价值的肯定与追求。三替公司在玩世不恭的处理问题的方式下,事实上解决了人们不正常的心理的种种问题。正如陈思和所说:“于观的‘三T’公司(替人排忧、替人解难、替人
④受过),本来是个荒诞剧,但在荒诞的现实生活中它又明明产生了实在的意义。”
与之相对的也就是作者明显持憎恶态度的是以《顽主》中赵尧舜为典型的一类人物,赵尧舜是那种典型的“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他虚伪、做作,外表一副正人君子、仁厚长者的风范,内心却是极其阴暗和卑劣的。作品写到赵尧舜的虚伪做作、假充仁人长者时是这样描绘的:“马青他们要耍弄赵尧舜说要为一个淹死的孩子开追悼会。赵尧舜说:“看来你们每天的工作确实没意思。这不奇怪,像你们这种人,没受过什么教育,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在社会上备受歧视,内心很痛苦,但又只好如此,强颜欢笑。这不公平,社会应该为你们再创造更好的条件。我要大声疾呼,让全社会都来关心你们。我已经不是青年了,但我身
⑤上仍流动着热血,仍爱激动„„。”俨然一位长者的派头。而当作品写到赵尧舜内心阴暗卑劣时:赵尧舜为了报复于观马青他们,故意用公用电话学着别人的腔调辱骂于观的父亲,用心何其歹毒下作。前面已经说过作者对《顽主》中的人物形象是有明显的爱憎的,对于赵尧舜这一类人他是憎恶的。在这其中其实蕴含着作者很深的思想那就是“反精英论”和揭示社会中一部分人人性的虚伪和扭曲。从书中我们可以读出赵尧舜教训于观马青杨重时俨然自己一副全能上帝人类精英的架势,王朔对此是恨之又恨的。王朔在接受采访时也不止一次地提出“反精英论”,他认为这是违背众生平等的原则的。这就很有力度地刺痛了社会上一些自诩为精英的所谓学界名流。而且王朔一向标榜“真善美”,反对社会中人的人性的虚伪,这也是对社会净化风气文化起到积极作用的,从这一点来说王朔的小说《顽主》是具有很强的先锋性的。其次《顽主》中人物语言的颠覆性也是具有先锋性的。
在这部小说中王朔秉持了以往小说的语言调侃中略带几分戏谑和讽刺的风格。这主要体现在三个顽主的语言上,而这种语言风格则是为许多评论者不足称道的,因为这些人物的语言是带有消极和反叛色彩的,是难以给读者带来传统正面的教义的,因而遭到论者的严厉批评。我是不这样认为的,通过深度开掘这部小说,你会发现作者之所以采取这种语言风格并非为哗众取宠,而是在有意把那些传统观念认为庄严神圣的东西狠狠地调侃戏谑一番。鲁迅说过:“喜剧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悲剧是吧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王朔则不同,他所叙述的既非喜剧也非悲剧。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个场景更像是一出出闹剧,他给闹剧也在无形之中下了一个定义就是“把庄严地东西戏谑给人看”。这就使得王朔小说的语言具有很强的颠覆性,对于庄严地事物的戏谑也表明了作者对传统信仰的否定——不相信以前的一切事物。引用《顽主》中的一句话就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我觉得任何事物在它初生时是难免过激的,新文化运动不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吗?矫枉势必过正,王朔小说语言对神圣庄严事物的颠覆性也正是他的先锋性所在。
如前所述王朔是在有意颠覆解构原先庄严地东西,这在小说《顽主》中俯拾即是。如:“你们这几个里我发觉杨重风度最好,比较深沉。”“得得,哥们,你别骂我。”杨重拍拍宝康的肩膀“我知道我傻”。这是对深沉这一词语的颠覆与解构。如:“我豁出来了,工作也辞了,不惜一切也要促成这个万人大餐厅,咱不就为了把事办成吗?不惜浪费!长城当时不也是劳民伤财么,现在怎么样?全指着它抖奋了,干就干史诗性的东西。”长城如此庄严神圣的事物也在三言两语间被颠覆与解构。再如:“我只知道凡事都有个理儿,打个喷嚏不还能写几十万字的论文得了个博士?”人家不叫喷嚏,这是粗俗的叫法,人家叫“鼻粘膜受到刺激而引起的一种猛烈带声的喷气现象。”这是对如今小题大做自命高明的学者知识分子的颠覆与解构。
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语言都是幽默与说理兼具,文采与嘲讽并存。以于观为首,三位男主角,其他人物也不甘示弱。在对话中,以一种反讽或挖苦的说辞表达了内心真正的情感态度。例如几个精彩片段:
1、马青与训夫妇女的对话: 训夫妇女:“„„往那一坐屁股发沉两眼发亮跟抽水马桶似的一拉一肚子花花肠水,早知道你有这特长,中苏谈判请你去呀,外面八哥儿似的,回家怎么一见我就没词了。” 马青(替夫挨骂):“我改。” 训夫妇女:“改,改屁,这辈子除了尿炕改什么了„„”
2、杨重与刘美萍的对话: 杨重:“这么说吧,我只要像王明水那样陪您一天。” 刘美萍:“您能像他那么善解人意、温柔体贴吗?”(以至于找人替他约会,又一种讽刺)杨重:“要说丝毫不走样,那就该出事了,不过我尽量遵循人之常情吧!” 刘美萍:“他答应给我买皮大衣的。” 杨重:“唉呀,我们公司这个业务还没开办呢!” 刘美萍:“哼,我说过不会一样的。”
3、于观与投资家的对话: 投资家:“万人大餐厅,那得多壮观呀!一旦在中华大地拔地而起,那什么劲头,甭老觉得外国月亮比中国圆,当初修长城的时候,现在呢,长城成中国人领带了。要干就得干流芳千古的事。” 于观:“万人大餐厅,又是故事。” 投资家:“这不是故事,已经谈得差不多了,花旗银行。” 于观:“这不可能吧,你当这是中国人民拿钱给越南打美国佬呢?” 4、投资家:“你对目前世界情况还不大了解,这无产阶级队伍人没少,这资产阶级队伍也 在壮大。”
于观:“中国银行从来不为这种野鸡项目担保。” 投资家:“我就是抱着办不成的决心来办这件事的,办成了,锦上添花,办不成,也在我预料当中,总之,我对前途永远充满着信心。”
如果前两个还是女人的伶牙俐齿的话,最后一个应该算是编剧借人物之口来讽刺社会及那些空想家了。其他诸如宝康、赵尧舜、方言知识分子等道貌岸然之流也是满口仁义道德、人生说教。在说话上都没有按照正常的思路想什么说什么。总之,人物语言丰富多彩,但却都不落于粗俗、鄙陋,不同于一般的泼妇骂街、满口脏话。事实上,这源于他们内心的一种忠诚的情感态度。在这些华而不实的言辞当中,反映出的恰恰是他们对于内心真正的情感态度。例如刘美萍在心里对真正男友的感情,训夫妇女对丈夫的感情,投资家对于事业、未来的执着之情等等,不管他们在形式上、外在上表现如何,事实上并没有背离内心的情感。甚至于于观父亲粗暴严厉的表象背后也含有对儿子生活与前途的担忧。
小说的男主角是三个,而这三个的中心人物是于观,也是最能言善辩的一个。杨重的语言偏向正统、讲理些。而马青则蛮横、狡辩、浮躁中夹杂着愤怒。于观是亦正亦邪、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典型。不管是具有人格分裂倾向的汉子,失恋痛苦的刘美萍,迂腐虚伪的赵尧舜,甚至于对严厉僵化又虚伪的父亲,在于观这里都分层设色、各有说辞。处于杨重的讲理与马青的无理之间,最懂得灵活变通。但是,在对待感情时,于观却是最认真最用心的一个。如果说杨重和马青在面对刘美萍时还有些逃避与玩弄的成分,那么于观在面对丁小鲁时是没有丝毫的伪装。在丁小鲁劝他生活要规律时他说“反正我也不打算活一百岁,管他好不好”,隐藏着对人生无常的看透。于观作为顽主的代表,怀疑一切,嘲讽一切,否定一切。却唯独对这份感情认认真真,影片中有个经典片段非常能说明这一点。
于观三个从电视看到赵尧舜对他们人格恶俗的诬蔑,特别气愤。关上电视。这时候丁小鲁正好打电话给于观。
丁小鲁:“是我,小鲁,告诉你个好消息。” 于观(自我嘲笑的表情):“哎哟,我可有日子没听到什么好消息咯。”
丁小鲁:夜大要招生了,有个专业挺合适你的。于观握着话筒没有说话,抬眼往上看了看。
丁小鲁:“喂,喂。” 于观:“我说,咱俩分开算了,分开吧,小鲁„„” 这时候于观的表情已经能看出无奈与乏力。
丁小鲁:“下午在老地方等我。”挂了电话。于观握着话筒,表情似乎又高兴起来。在面对现实乏力无助时,于观不想让丁小鲁跟着自己受到别人的轻视,所以想要分开。但是在他坚强无畏的表象背后却是一份依赖爱情的柔软的内心,所以他并不是真的想和丁小鲁分手。在和其他人说话时于观特别擅长神侃,但是在和丁小鲁在一起时往往说话很简单。因为了解,因为找到了精神的归宿。正像刘震云所说:“真正了解于观的大概只有丁小鲁了。他的人物可以调侃一切,但决不调侃爱情。”王朔自己也说:“他可以一天到晚胡说八道,但 ⑥总有个时刻是真的”。他们选择用调侃的谈话方式来轻视谈论的内容,但并不意味着他们丧失了对待感情时的忠诚的态度。相反,在他们热衷于亵渎神圣、嘲讽规范的同时更加衬托出对于内心底层对于爱情的渴求,对于爱情认真的态度。
作者为何刻意的把一个个庄严的事物统统颠覆。这绝非作者贪图一时口快。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王朔无疑透视到了在社会转型时期处于这一时代的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人们价值观的迷失与扭曲,以及人性的虚伪。把傻等同于深沉,解构长城的民族文化意义,对学者的嘲讽,其实反映出一个社会非常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对一切事物的价值重估问题。”这是时代人所共有的心理,王朔是一 位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用他的小说婉转地提出了这一社会问题并相应的表达了自己的倾向。
再次就是叙事风格的亲切随意和情节安排的高度生活化也是具有先锋性的。
王朔的这一创作风格使得他的小说不再是作家写作给读者来读,以使读者获得某种启迪和教义的东西,而是作家在与读者分享。它拉近了作者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这就同时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读王朔的小说你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畅感和轻松感,你不会有文字的障碍和来自各方的压力。王朔曾说:“作家不应有什么优越感。”我是赞同王朔的观点的。五四以来,作家大多是以启蒙者的姿态指点着芸芸众生的,没有几个贴紧群众的平民作家。就是文学大家鲁迅,他的作品在当时又能为多少民众所熟知呢?王朔的作品通俗流畅极富生活化,调侃中略带几分幽默,虽失之严肃,却不乏深刻。其实严肃的东西不一定就深刻,没有谁规定过作家和思想家一生下来就是板着脸的。王朔小说的这种亲切随意和高度的生活化在小说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如:“众人七手八脚包饺子时老太太建议给干活的人放点曲子。”丁小鲁拧了半天老式箱形收音机旋钮,调出一组豪迈缠绵的出征歌曲,这些歌曲也是流行歌曲,大家都随着旋律摇头晃脑地哼哼。当歌手唱到:“如果是这样,你不要悲哀。”三个男人一齐昂首唱第二声部——:“我不悲哀!”这种非常生活化的语言读来是非常亲切真实得。王朔小说风格的亲切、随意和高度的生活化为他赢得了众多的读者,这表明它满足了当今时代读者的需要。还是那句话“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王朔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发展,他的小说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他小说先锋性的很有力的佐证。
时至今日,王朔已不再是单指一个人和几部小说,他已成了一种现象,一种文化的旗帜。某种新生事物的出现绝不会空穴来风,需要我们去认真地对待。研究这些,对于文化的多元化健康发展和社会精神文明的进步都将大有裨益。
注释:
①(中国)王朔:《顽主》,第1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②(中国)王朔:《顽主》,第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③(中国)刘小枫:《拯救与逍遥》,第3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④(中国)王朔:《顽主》,第5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⑤(中国)陈思和:《黑色的颓废——读王朔小说的札记》,《当代作家评论》,第19页,1989年第6期。⑥(中国)王朔:《我的最大弱点:爱自己,而且自己知道——答何东问》,参见《无知者无畏》,第171页,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参考文献:
1.陈思和:《黑色的颓废——读王朔小说的札记》,《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2.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版。3.王朔:《无知者无畏》,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主要参考小说:
浅谈王朔小说的叙事特征 第3篇
一、视角定位审美享受
什么是文学的叙事?简单地说, 就是话语虚构社会生活事件过程。叙事话语即叙事作品中讲述故事的语句。王朔的大部分作品中都用第一人称叙述的视角, 即“我”眼中的世界是现实的视角, 这个人物作为叙事者兼角色, 他不仅可以参与事件过程, 可以离开作品环境面向读者进行描述和评价。这种双重身份使这个角色不同于作品中的其他角色, 他比其他角色更“透明”易于理解, 八十年代以前的小说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 大都基于一种善与恶、正与邪、进步与落后的二元对立模式, 而王朔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大多是油腔滑调整天无所事事的地痞流氓形象, 是一些中国的“嬉皮士”。在叙事者“我”的眼中,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压根儿就不存在所谓的精神“庄严性”“神圣性”, 有的只是实在性、功利性和平庸性。
《一半事海水、一半事火焰》中的“我”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罪犯。“我”们是一群在新社会条件下产生的边缘人, 活着对“我”们来说只是为了玩, 一切都只是游戏, 成为真正的顽主, 游戏人间。“我”们是一群顽主, 所以不会放弃任何带有游戏和冒险的机会。正如《玩的就是心跳》中的方言所说的“我是从不放过当主角的机会的”。这些小说中的“我”脱掉以往小说中华丽的外衣, 把人性最原始的另一面揭示给读者看。鲁迅曾说过悲剧是将人生有意义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那些被中国传统的正人君子所不齿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丑事, 却成为这些叙事者“我”的日常生活的主旋律。即使写爱情, 也不像以前小说中所描写的温情, 王朔小说男女之间的爱情一反传统的模式, 他们之间只有性而没有爱可言。《空中小姐》《浮出海面》写八十年代的男女之情痴情女子负心汉, 然而, 在这两部作品中却能看到王朔对自己切身的生活经验和社会感受的自我表现, 两部作品的男主人公都流露出作者的影子, 很大的程度上有一定的自传成分。正如《空中小姐》中所描述的男主人公“我”脱下紧身束腰的衣服, 换上松弛的老百姓衣服, 几乎手足无措了, 走到街上, 看到一种生活正在迅速向前冲去的头晕目眩。而我如今却成为生活的迟到者, 茫茫然的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然而他们这些生活的迟到者却不想去追赶, 不愿在原来的价值轨道上运行了。因为他们发现原先的价值观已经荡然无存, 正统的失落, 使平凡、诚实是乏味、无能的代名词, 而金钱成为唯一真实可信的东西, 他们在这种状况下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于是成为社会上的“多余人”, 自身的价值得不到实现, 于是就开始混日子, 生活日新月异的变化, 然而他们内心却更加的孤独, 一种油然而生的失落涌上心头。王朔小说以其独特的视角观察着当时的人群, 这种特殊的生活方式是主人公自己的选择, 也是王朔内心最深层的体现, 那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他笔下的人物有其独特的个性, 然而这些“多余人”最终体现当下社会的价值取向。可是, 他们并没有在轻松中得到社会的认可, 却有着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失重感。这种失重感带来他们整体体验的孤独, 这些顽主们像城市的马群一样成群结对在城市里流浪, 所谓的哥们只是在行为上的一致, 他们共存的空间只是缓解了暂时的个体焦虑。他们彼此并不能分担孤独与焦虑, 聚集在一起反而增加了另一份孤独感。当群体解散后个体的焦虑便会浮出海面, 体现生命的狂欢, 于是“我”成为独特的“这一个”。王朔的这种颠覆传统的第一人称叙事视角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 给我们不一样的审美享受, 这也是他在九十年代如此受大众欢迎的原因之一, 他笔下主人公的反叛精神是隐藏在作者叙述的字里行间。
二、异样语言彰显魅力
王朔小说独特的叙事特征还表现在他调侃的语言上, 相对于老舍, 王朔与北京血源要淡些, 他是新北京的第二代移民, 因而形成了一种被称为“新京味小说”的文体, 这种“新京味小时”当然按时相对于老舍的京味市民小说而言的, 虽然都是以北京市井语言为底色, 但是热爱淡化了老北京市民的“胡同”与价值, 却融入了北京青年之间流行的一种语言, 如《空中小姐》《浮出海面》《橡皮人》等, 这里的年轻人一口流利的京腔, 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情感, 语言不仅体现作家的表达方式, 而且体现作家发思维方式。王朔小说中的人物语言走出了老舍语言的“正经”变得玩世不恭起来。如在《一点儿正经没有》里说了几个所谓作家之间的事情。他们高谈阔论的调侃了一番我们视为神圣的东西。如:“文学家的基本功是什么?”“说学逗唱.什么都得感兴趣, 什么也干不好。屁股得沉做得住;眼睛得火好事拉不下;脸皮得厚祖宗八代的龌龊事都得打听;腿脚得利索及时避枪口。”这种语言是一种不动声色的对传统语言的颠覆, 剩下的只是语言的狂欢, 把传统语言作为调侃的对象, 这样他小说的话语对传统的叙事话语有着本质的颠覆。
《千万别把我当人》里有许多精彩的对话, 一针见血地折射出社会的一些现象。如:“下面我问第二个问题, 还是这张卡片, 这只猴子和这个人, 是猴子的脸皮厚呢还是人的脸皮厚抑或是一样厚, 请你回答?”“人脸皮厚”“回答错误, 扣分”“没错, 是人脸皮厚么。猴子的脸老是红的而人几乎不红, 明显厚于猴子。”“你错了, 应该说猴子屁股老是红的, 当然问题不在这儿, 我问的是脸, 这一题的正确答案是猴子的脸皮厚因为人没脸皮!”这些语言是王朔对现实的讽刺:人的脸皮没有猴子厚, 那是人根本就没有脸!那之能称之为“面部”, 是人们平时都带着的一张纸, 没有感情, 没有自尊的面目而已!可见王朔通过玩语言, 来解释社会上的一些普通现象, 市场经济下大多数人做了金钱的奴隶, 迷失了自我, 连最起码的人性也消失了。讽刺那些拜金主义的心理不健康, 他们为追求物质享受无所不用其极, 王朔用露骨的语言宣泄了内心的不平。
王朔的小说得到大众的接受, 它真正显示了反讽的效果, 反讽在王朔小说中的意义, 集中在文化传统与反传统基调的相互交融配合。处于叛逆时期的青年, 对一些个性语言有敏感, 他们往往会仔细阅读汲取其中的精华, 王朔根据自身的的理解, 有自己独特的语言系统, 通过其特有的调侃和幽默, 实现对文化传统的反叛, 对语言传统的改造, 从而达到对现实生活的强烈的嘲讽和亵渎。
三、结构设置隐性背叛
人们所认识的社会现象是杂乱无章的, 要达到有秩序的认识就要掌握现象的结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必须洞察内在结构, 才能领略作者的真正意图。表层结构是可以感知的, 深层结构则是潜藏在作品中的模式, 必须用抽象的手段把模式找出来。罗兰.巴尔特认为文学也是一种语言, 即一种符号系统, 它的本质不在他所传达的信息里而在该系统自身之中。我们要找到隐藏在文学表层背后的深层意义。因此深层结构是作者潜含的文化意义, 根植于一定文化中的深层社会心理, 呈现出多义性。王朔小说的表层结构都是很浅显, 按历时来展开情节, 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发生, 从开端到发展再到结局。每个故事似乎都差不多, 但这种表层结构下去隐藏着深层意蕴, 这种深层结构打破历时来展开情节, 按共时来体现具体叙述话语产生的深层意义。王朔笔下的一些顽主表面上看一群玩世不恭的“痞子”, 但深层意义上是反映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端, 作者想用调侃的语言, 揭示社会所存在的丑恶现象, 引起人们的注意。在《一点正经没有》里, 一些连文学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居然就玩起文学而且还“责任的很”“依着你, 教点人民什么好呢?怎么过日子?还不用教吧?”“得教!告诉人民光自个日子好过了还不算本事, 让政府的日子好过了才是好样的。”“政府说过着话吗?别忘了政府可是为人民的。”“当然, 要不要我们作家干什么吗?就是让我们把那些一说就炸一说就翻脸的话拐弯抹角柔声细语地对人民呢喃着。”这些话表面看来是一种恶意的调侃, 事实上, 它却是对真实生活的一种折射, 将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丑恶用夸张和变形的艺术手法呈现在读者的面前。作者以一种“荒唐”来隐喻真实, 借“胡言”寓真意的调侃嘲弄, 从而获得极强的反讽艺术效果。他的作品中隐藏着对现实社会的揭露与批判, 这种批判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理性判断, 所以王朔是八十年代形成的顽主们在文化上的代言人, 他们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的清醒认识。
王朔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含义与深层意蕴构成了一种张力, 让读者在阅读他的作品时, 被他那种张力所吸引, 让内涵与外延得到有机的结合。从而很好的为他所表达的意义服务, 给人一种新鲜, 复杂感。他的小说充满的侃言, 某些语言有复义的现象, 他的语言就是有多义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样才能更好的吸引读者。王朔曾经说过:“当权威仍然是权威时, 不管他的错误多么确凿, 你尽可以复语, 但一定千万不可当面指出。权威出错误如同列车脱轨, 除了眼睛看着它一头栽下悬崖, 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挽回, 所有努力都将是螳螂挡车结果只能是自取灭亡。”这些话中隐喻着对传统文化的嘲讽, 作者正是用他那特定的语言与手法来完成他所预期的目标。每一个语句被用到他的作品里, 不仅承受着作品整理构思所形成的特定语境的压力, 它自身依靠字面组合所产生相对稳定意义也起到作用, 这就是王朔小说的魅力。
结语
王朔的小说是值得我们认真品读的, 他内心的忧患和悲凉成为他创作的主调。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语境中, 社会历史语境的宏大的启蒙叙事在当代文学中“终结”了, 文学进入了又一个新的时期。他异样的视角、调侃的语言成为当代文学独特的“这一个”。
摘要:王朔以富有个性色彩的叙事话语建构艺术世界, 为当代文学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这对小说叙事的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他用独特的话语构建自己小说的人物形象, 以调侃的语言为顽主们润色, 让我们体会异样的风格, 这种玩世不恭、消解崇高的叙事方式有其现实语境, 提供了文学的公共空间。
关键词:王朔小说,边缘人,调侃语言,深层意义
参考文献
[1]温儒敏、赵祖谟.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1.
[2]王朔.我是你爸爸/王朔文集[M].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3]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 (第2版) [M].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